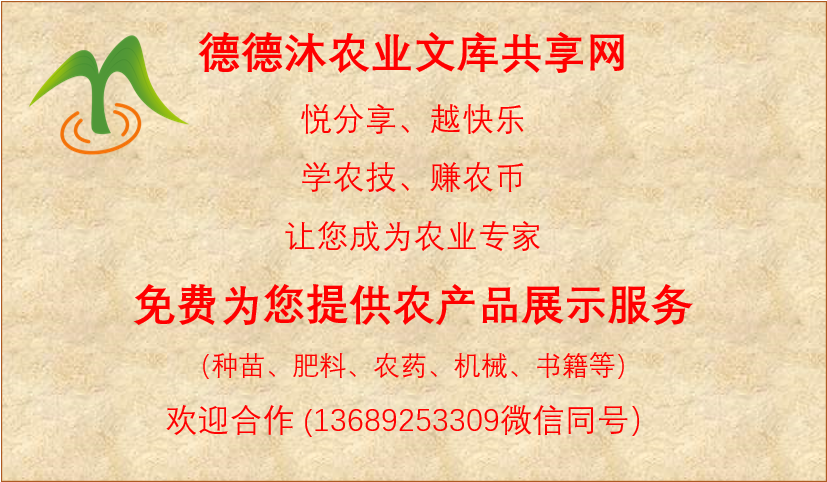在中国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做重大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切不可把有机农业狭义地理解为一种不同于化学化农业的生产模式,而要提高为一种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
因此,我们主张有机农业的从业者、特别是企业,不能只关注生产和销售,而要自觉地融入“社会化”,这样才能在这个国家的生态化转型中积极参与到与生态化有关的社会活动之中。
众所周知,有机农业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被认为是一种相对资本主义大规模农业造成严重“负外部性”代价而兴起的社会运动;在中国事实上也应该是社会运动,只不过在现象层次上针对的是产业化农业的质量安全问题,却不得不在本质上受制于产业资本主导的制度体系那些标准化和制式化的约束。
这个各界广泛参与的社会实践虽然很丰富、很国际化,但也应运而生着很多直接影响着有机运动走势的部门化观点,很多参与有机农业的单位和个人仍然时不时地被那些工业化时代流行的指标体系和审核方式困扰着,越是按照这些工业化时代内生性的指标体系去做一产领域的农业生产,越是亏损得欲哭无泪……
01 数千年生态农业被全面颠覆
我们且不去参与坚持停滞在工业化时代的那些技术专家们关于有机标准的争议,不妨先从“有机农业”概念说起。
胡跃高教授长期从事有机农业的研究与实践,从胡老师新书里所提出的资料看,一方面,如果从西方人在1972年组建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成立算起,47年时间有机农业已扩展到了世界170多个国家与地区。
有些人觉得有机农业是个有特定标准的、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农业模式,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实践活动也必须符合西方提出的标准,也因此就有了官方、社会组织、企业等三类不同机构的、需要按年收费才能做出的所谓“有机认证”。
此外,还伴随着很多研究者们据以获取科研经费的“科学成果”。如果仅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看有机农业,其发展态势确实不容乐观。
胡老师书中资料指出,2013年世界有机农业总面积为4300万公顷,约占世界农用地面积的1%。其中非洲占0.1%,亚洲占0.2%,欧洲占2.4%,南美占1.1%,北美占0.7%,澳洲占4.1%。比较而言,澳洲、欧洲发展稍好,其余各洲发展基 数低,行动缓慢。2005年亚洲有机农业生产面积为268万公顷,2013年为343万公顷;北美2005年为222万公顷,2013年为305万公 顷,呈持续增长态势。
2016年统计,全球有机农业发展农用地面积为5800万公顷,生产者为270万户,全年产值900亿美元(FiBL&IFORM,2018),有进一步发展。从全球占比 考虑,其利用的农用地面积占比不足全球的 1.2%,农户数不到1%,产值不足总量的万分之三。这些情况标示出,世界有机农业探索100多年来,发展形势并不那么兴旺。
1989年,中国还没有大面积搞化学化农业的时候,正式加入了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但若不那么刻意地坚守“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体系,则会认为这不应该是有机农业正式引入中国的起点。因为没有推行化学化、机械化的农业原本就是生态农业,尽管有机农业也在常规意义上关注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基本属性,但生态农业与自然界一致的多样化在性质上远远高于从西方引入的有机农业概念。
若从经验过程看,中国只是20世纪70-90年代对西方开放以来才从海外大量引入化肥农药生产线,同时还大量进口农用化学品;由此造成的各级有关部门借此获取财政资金的“成本上推”的内在机制,迫使我国农业陷入资本深化的困境——即使实现了高产也无法抵补不断追加的成本。其中,真正的获益者只是那些利用内外的利益扭结而上下其手的投资人!
无论主流精英如何说教,人们看到的最基本的事实是清楚的——用工业化改造农业的短短几十年间,中国本来维持了数千年的、以最少的资源养活世界最多人口并且维持资源环境可持续的生态农业模式受到全面颠覆。
02 中国有机农业实践者突破禁区
就是在这个误以为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就是现代化的主流利益群体推进的巨变 之中,中国社会化的有机农业实践者被迫选择突破禁区、开拓创新,在有机农业保障粮食安全问题与乡村社会安全问题上开展探索。
蒋高明、安金磊、朱安妮、邱建生、石嫣、严晓辉、闫洪明、刘小平、吴向明、李云凤等一大批实践者,先后在粮食作物、蔬菜水果、畜牧养殖等领域的质量效益型转变,以及稳产高产上取得重要进展;“有机好吃不减产”观念成为中国有机农业实践的口号。
最近20年来,社会创新和大众努力已经成为普遍趋势;同时,也使中国今天有机农业耕地面积占世界第一,会员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产值占世界第四。
进一步,如果人们愿意从另一个视角出发,自觉地把中国21世纪正在推进的生 态文明战略转型结合起来,就如同社会上很多人认同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必那么遵从 “西方中心主义”地去界定所谓标准化、标签化的有机农业,则有机农业不仅会使人们从关注狭义的农产品质量问题形成一种安全生产这种最低层次的要求,演化为最高层次的新时代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甚至由此而成为与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结合的三农主流,使之成为一种绿色活动,广泛遍布于城乡中国。
因为,所谓有机农业为基础的生活,在亚洲原住民社会本来就是被生态、生活、 生产“三生合一”的生存方式所内在决定着的一种文化传统。当代人只需坚持贯彻中央2007年确立、2012年作为国家战略内在要求人类自觉与自然多样性结合的生态文明, 则有机农业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主流,并且本源性地、自然天成地内生于这种人类与自然界共同具有的多样性直接结合的自觉努力之中。
03 加强有机农业的社会化和生态化
由于我并非这个领域的专家。仅以一个普通人的思考能力,我倾向于加强有机农业的社会化和生态化。我们之所以希望有机农业融入生态文明,也是从这个社会事业如何实现可持续来考量的。
因为,若从人类告别蒙昧进入文明算起,农业就是内在着“三生合一”文明的载体。这个世界原生态的农业最初形成于亚洲的东西两端,西边是流域面积狭小的“两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小麦为主粮作物;东边是流域面积广大的“五河(辽黄淮长珠)”,因气候和地理条件差异很大而有黍稷稻粱等多种主粮作物。
表明了人类最初进入文明时借助于农业,本来就顺遂大自然而内在地具有着所谓“有机”农业的基本属性。这样算起来,有机农业已经有至少上万年的历史。
至于近代为什么是西方人强调有机农业,乃在于他们进入工业化的时间比我们早,因而离开传统农业太久。自17世纪开始,欧洲在长期贸易赤字压迫下推进海外殖民化掠夺;之后19世纪又为了统治世界贸易而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到20世纪首先在美洲殖民地为了这种大面积生产方式而在农业领域大量使用工业品,由此而最大化地形成了面源污染和资源破坏;遂有部分西方人士反思转型为支持“有机”农业……
如果没有西方主导殖民化而使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恐怕至今仍处于“三生合一”的有机生活之中,也不必跟着西方人担忧“全球气候灾难”。诚然,此类“三生合一”的生态文明会被或明或暗地认同并且追随资本主义的主流认为是落后,必欲除之而后快!
从发展中国家现实来看,二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打疲了、控制能力弱化,世界范围内才形成了一百多个民族国家。随后,人口增长,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原来属于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随即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现代农业,人们走马观花于欧美,往往更青睐解决粮数量型安全上相对简单、高效、易操作的常规现代农业。
由此,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大力购买化学化产品,甚至以对外负债的方式直接引进化肥农药生产线,这些都造成农业的高负债压力下的“成本上推”,迫使农业全面化学化来追求产量,也就由此成为高污染的现代化农业在发展中国家中坐大,甚至颠覆了生态农业的基本原因。
然后,在农业造成大规模面源污染和严重食品安全事件的冲击下,才能有条件由部分人推进向“有机农业”的转型。
总之,因为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已经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结构,仅一部分人做出努力也是有限的……
在中国,放弃“三生合一”的过程也大致如此。由于1840年被西方人打败之后开始了最近一百年的激进工业化历程,到1980年工业化初步实现就开始在农业领域推进化学化和机械化;遂在20年后造成农业成为中国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面源污染。
诚然,也有很多人会认为,传统的“三生合一”的农业过于落后,肯定没有现代化大生产更有效率。他们的论点最大的缺憾是没有看到资本深化的农业大生产所造成的严重得多的“负外部性”——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以及食品的质量下降甚至毒化……
激进现代化农业客观上造成了多重“负外部性”恶果,已经影响党群关系和社会稳定;不过,中国人通常会“变坏事为好事”。例如2008年前后的“三聚氰胺事件”“孔雀绿”“苏丹红”“毒大米”……
中国食品安全、粮食安全、乡村社会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国际农业安全五大问题并存。从历史发展角度审视,中国农业正处于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的风险之中。
04 生态文明转型与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古代哲人相信客观事物的变化遵循“否极泰来”的规律。也就是在食品安全事件叠发的2008年,中国确立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农业发展目标,进而在2012年确立了“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同时强调美丽乡村,到2017年则要求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全面转向“绿色生产方式”。
国家向生态文明做战略转型时期的政策环境重大变化,促使大多数中国人有了寻根溯源的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搞亩均化肥超过世界均值6倍、农药超过4倍的高污染生产呢?到底是谁或什么机构为了一己之私利在破坏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明传承下来的“三生合一”?如果激进而颟顸的利益集团们不那么粗野地强迫本来就是国家安全基础的农业也去追求GDP,那我们本来都长期生活在有机农业为载体的生态化食物体系之中。
中国和世界上的有机农业实践,虽然仍处于广泛分布的小规模发展的经验探索阶段,却代表着人类走向生态文明这种全局意义上的开拓创新,只要得以纳入国家政策扶持,就可能很快满足社会经济与生态发展相结合的需求。
在这场开放式的农业可持续道路的探索过程中,生物动力农业(活力农耕)、自然农法、CSA(社区支持农业)、永续农业、生态村、多年生农业、自然田野(Nature land)等新型农业模式先后引进国内,被各类机构和志愿者团队自发地做示范试验。国内各地有关方面到处围绕生态农业、绿色农业进行积极探索,大都取得一定进展。
总体来看,这类新型农业模式大都具有维护食品安全、重视生态环境的积极意义,但在早期未能有效带动农民作为生产主体的经济行为发生显著改变。于是,便有更多新型社会参与式的新业态借助城乡融合而蓬勃发展起来。
例如,借鉴国外CSA和慢食运动的“社会化生态农业”从2008年起步,十年间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进而,只要我们贯彻城乡融合的指导思想,充分发动广大市民群众跳出“消费主义”的迷思,推进市民群体直接参与到生态农业构建之中,客观上可以改变有机农业生产者过去独立承担转型成本的被动亏损局面。
例如,所谓CSA的实质,是让得到食品质量安全的市民向生产者支付、甚或预付维持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必要成本,同时分担自然风险及市场风险。从当前CSA大部分都没有发生那种一产农业严重亏损的事实看,只要实现农业的社会化,则有机农业的生态安全目标不难实现。
君不见,自中央确立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有关部门也从工业化制度体系改弦更张,明确强调“立体循环农业”“一二三产融合”等符合绿色农业的新业态。
生态文明转型与乡村振兴战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单独一个国家明确提出进行全人类意义上的文明时代建设,不仅已经正式写进宪法,而且中央确定由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直接承担领导责任,要求财政金融一切优惠政策向三农倾斜。
这些符合生态化转型的新政对于有机农业的推进作用无论怎么估量都不会过分。接着我们会看到,全域生态资源开发与社会化有机农业结合的这种生态文明的大道,势必在神州大地拓展开来!